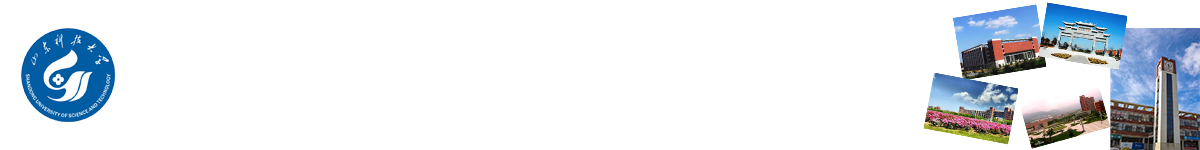文章详情
返回 我的父亲名叫段七星,今年80岁了,按照乡俗和我们的经济条件,应该为父亲举办一个盛大的生辰庆典。本着勤俭持家的古训和时代新风的要求,我们兄弟商量,一切从简,决定由我写一篇文章作为贺礼,来表达我们的拳拳孝心。
父亲出生在尧都区西头三泉村并在这个小山庄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他8岁进入私塾开始读书,时断时续。长大后,先后做过县长的通讯员、农会秘书、供销社营业员、钢铁厂装卸工。
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29岁的父亲被原平钢铁厂精简压缩回到村里务农。不久,经亲戚介绍认识了我的母亲。这年父亲29岁,母亲22岁。按照婚前约定,父亲要从西头三泉村迁往土门村居住,并且第一个孩子必须从母姓,以顶立王姓门户。母亲和父亲结婚前,通过法律手段从叔伯家追回了属于她父亲的那份房产,正是这份房产给家庭带来了无休止的纠纷。结婚后,他们住到了这栋房子,虽有法律作保障,还是引起了叔伯后代们的不悦。那是一座民国时期建造的四合院,属于我们家的是三孔南窑和一部分附属房产,院子里全都是用青砖铺的地。那时不准造新房,再加上经济不宽裕,有这样的房院确实算高标准了。
四合院中父亲是唯一的农民,收入很低,和挣工资的他们比,自然属于贫困户。虽然平日父亲为他们干了不少体力活,他们仍然瞧不起父亲。有时,因为一些琐事会发生一些纠纷,他们常常骂父亲是“招布袋”。生活在这样的环境,父亲感到很压抑。母亲是个很要强的人,自小失去父亲,很任性,有时不能理解父亲的难处,夫妻之间常常不和,甚至争吵打架。
父亲无奈时,总要回老家西头三泉村僻静几天。逢年过节,父亲经常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母亲抗争,以发泄心中的压抑。不管心里有多么憋屈,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父亲要参加生产队的各种劳动,挣工分养家糊口。慢慢长大的我,目睹了父亲遭受的种种艰辛屈辱与不公。作为一个农民,无论春种秋收还是严寒酷暑,从摇耧耙耱到出圈挑粪,举凡生产队的农活儿,父亲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父亲年少时没有干过多少体力活,是农村人说的“没有苦”,特别累的时候总要休息几天。身体上的累不算什么,他最难以承受的是别人的蔑视与不公。父亲不是本村出生长大的,没有儿时的伙伴,缺少“铁杆哥们儿”,是名符其实的“外来户”;外祖父去世早,没有老人荫护,他在村里没有地位,常受人欺辱。有时队里安排不好干的活儿甚至故意刁难,父亲稍有不从就会有拳脚的“礼遇”,挨打挨骂是经常的事。每遇到这样的情形,父亲总是长吁短叹,后悔自己年轻时不懂得选择和坚守。他常说过去如果怎样现在就不会这样,因而对我上学读书给予很高的期望,要求格外严格。
父亲在这样的环境中过了整整十年。1972年,父亲耙地时未站稳,被耙上的铁齿割伤了腿,只好在家休息。迫于生计,父亲用从爷爷那里学到的风水知识给邻居朋友看坟地,帮他们选红白喜事的日子,俗称“风水先生”,以期获得微薄收入补贴家用。这种行为在当时被称为“迷信”活动,为此村里把这件事情反映到公社。
不久公社领导在一次大会上点名批评了父亲,父亲顿感压力很大。生活在这样的环境,父亲有了改变处境的想法。恰在这时,父亲当通讯员时的朋友做了西头公社的党委书记,推荐他到公社去做事务长。离开了生产队,从挣工分到挣工资,父亲的心情总算不那么压抑了。但没过多久,有人提出父亲不是这个公社的人,这份工作不应他干。不得已,他去了公社所属的煤矿,先是做开票员,后来又担任该煤矿的采购员。
父亲对这份工作甚是满意,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心血,辛勤的工作换来了领导的充分肯定,家里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母亲也觉得自己有“地位”了,不时带着我和弟弟住在城里,全家人都很高兴。父亲挣了工资还有补助,每月能领到50元左右,必要开支后还有少量结余,从此之后不再欠队里的粮款了。
1975年我刚刚12岁,按照乡俗应当“圆锁”。家庭状况好转了,父母自然也想把我的生日宴办得体面一点。但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大队一名主任带人以“破四旧”的名义将亲朋好友送的礼物洗劫一空。对于这种行径,父母悲愤难当,深感屈辱。多少年来,偌大的一个村子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为此父母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父亲改接灯线,由于情绪不好致使灯线连电,烧坏了全家的电灯和电线,还差点弄出了事故。当时我年龄小,根本无法体会父亲此时的心情,他只是说了一句话:“‘出门人’真是不容易啊!”这件事使父母受到很大伤害,特别是母亲,半年之后就患上了气管炎,遇事一不顺,就喘不上气来。从此之后,父亲一边工作,一边帮助母亲治病。三年间一共住院十几次。
由于入不敷出,家庭经济状况又趋恶化,债台高筑,达2000余元。这个债务是父亲7年工资的总收入。在这个困难时期,我也成为临汾县重点中学———刘村中学的一名中学生。对于我的学业,父亲很是上心,不断为我创造条件,以使我安心学习。当他看到我在学校伙食不好、生活艰苦时,毅然决定让母亲到刘村中学附近租房居住陪我读书。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幸福,但好景不长,由于母亲的病日渐加重,她不仅无法照顾我的生活,自理都很困难,不到一年的陪读“幸福生活”宣告结束。
有病乱求医,母亲住院治不好病,只好求助巫师了。对于这个做法,父亲尽管不同意,但也只能听之任之。一次,母亲请了乡村的巫师做了所谓的“摆治”。没过多长时间,同院的亲属们突然患病,他们认为是母亲的这种“摆治”造成的,为此引起了母亲叔伯后代们的激愤。这次,父亲被叔伯的后代们打了巴掌。对此,勇于担当的母亲挺身而出承担了责任,但这个做法并不能改变父亲被打的事实。父亲只能用再也不回这个院子的行动表达自己的愤怒。
那时,我还年幼,对父亲的这种行为不理解,认为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母亲由于生病,心情不好,免不了对父亲的行为多有微词。似懂非懂的我听了母亲的唠叨,也认为是父亲不好,常常站在母亲的立场上指责父亲。父亲显得很失落,更多的时候则是选择了沉默。不懂事的我还认为是我和母亲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后来我才明白自己是多么幼稚啊!
父亲为了照顾母亲,被单位领导多次“约谈”,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向煤矿辞职。当时父亲只有45岁。回到家里,父亲既要到地里干活儿,还要悉心照料母亲,更要从头学和面、起面、蒸馍、炒菜,洗衣、熬药,每天与锅碗瓢勺打交道,都是简单的重复。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其间的煎熬与甘苦,他都默默承担下来,真是委屈了他。好心的亲戚看到父亲这样的艰难,提出让我辍学的建议,对此父亲断然否决。他说:“只要孩子们愿意上学,我再困难,也不能让他们断学。”
尽管父亲一再用心和努力,母亲的病情还是每况愈下。1980年12月29日,得了5年病、只有39岁的母亲撒手人寰,永远离开了父亲和我们。当时,父亲只有46岁。由于父亲下岗几年一直没有工作,家中没有经济收入,母亲安葬时,只用了最差的柳木棺材,还借了债。那年春节,我们父子三个光棍度过了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之前过年时,母亲尽管身体有病,还可以坐在炕上教我们剁肉、调馅、包饺子。如今,活儿还是那样的活儿,但包出的饺子却不成样,从锅里捞出来,全变成了“开口笑”。看着眼前的一切,我想到了母亲,忍不住先哭了,弟弟也哭了。父亲很难过,说:“明年我会把饺子包好,不会再让你们吃‘开口笑’的饺子了。”
那个时候,恰好赶上了国家发展经济的新时代,父亲利用过去的老关系,做起了贩煤的生意,这也使我认识了煤炭并献身煤炭。那时,我正在临汾一中复读,目睹了父亲的艰辛和不易。1982年的暑期,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山东矿业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开学时,父亲把全部的积蓄拿出来,把所有值钱的家当都变卖了,硬是把我送到太原。看到我坐上东去的列车,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分明感受到他对我的殷切希望和望子成龙的期盼。大学四年,父亲的脸上增添了许多皱纹,头发也灰白了许多。上学期间,为减轻父亲的负担,我勤工俭学补给家用,父亲不放心,怕影响我的学习,又专门来学校看了一次,对我说:“不要干这些,我再困难也要让你读完大学。”那次送他回家到济南换车时,我第一次提出让他为我们找一个后妈,他一口回绝:“绝不给你们添这个麻烦。”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忻州的原平,父亲很高兴,因为这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报到之后,父亲立即为我完婚。第二年,我的第一个孩子在矿务局医院出生了。父亲当了爷爷很高兴,提前来到了我的工作单位。他每天往医院送饭并为孙女洗尿布,承担了一位爷爷不应当承担的责任。孩子过了满月之后,他才回家。
父亲上过学,虽然时断时续,但他知道只有读书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对于我的学习,他要求非常严厉。在我的记忆之中,父亲因为上学打过我两次。一次是我上小学时和同伴逃学,父亲打得我尿在床上;一次是我上高中时,因为考了班里的最后一名,私自决定回家复读,父亲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打了我一次,使我感到很没面子。为此,我还记恨了他多年。现在想起来,是父亲的“铁石心肠”改变了我的一生,也使我明白了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应该坚持和坚守。
1988年5月,为给父亲和弟弟增加收入,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我和妻子帮助他们贷款买了一台东风牌大货车,但由于他们经营不善,不得已我只好调回临汾供销机械厂。那时,我一边工作一边帮助他们经营。汽车晚上放在妻子的厂里,每天一早就要出车,时间长了门卫有意见。父亲就主动提出他来厂里做门卫,一方面可以挣几十元的工资,另一方面又可以给自己家的车提供方便。冬天行车,每天晚上都要放掉汽车水箱中的水,一大早就要给水箱加热水。那些工作都是父亲一人完成的,当时,父亲已经将近60岁了。
过了两年,家里的房子修好了,车不用在厂里放了;弟弟家也有了两个孩子,父亲又回到村里,帮助弟弟带孩子并耕种家里的几亩地。1993年,我在煤管局办公室工作,迎来了父亲60岁的生日。那时候,父亲的身体不是很好,我邀请了部分好友为他举办第一次生日宴。从那以后,父亲每年的生日都会有许多亲朋好友前来祝寿。那一年的生日宴结束之后,我第二次提出为他续弦,父亲没有反对,只是说等等再说。
1995年9月,我担任了临汾市煤运公司经理,为了侄儿们上学,弟弟全家也搬进城里,只剩下父亲一人在村里。我第三次提出为他续弦的事,他终于答应了。那一年的国庆节,我邀请了部分亲朋和好友为父亲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那时,母亲已经过世将近15年了。15年中,父亲既当爹又当娘,备尝艰辛。回忆起那艰苦的岁月,我们怎能不感恩这如大山一般的父爱!
父亲组成新的家庭之后,一直住在村里。起初的几年里,他一直耕种村里的那几亩地。1999年之后,父亲年龄过了65岁,我劝说了几次,他终于同意将土地的使用权无偿给了原来的邻居。这样,父亲每年冬天住城里,清明节之前又回村里去住,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这些年,我和弟弟的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村中的几间门面房也交给父亲打理。逢年过节和父亲的生日,我们都会给他一部分钱并购买新衣。那些钱父亲一直舍不得花,新衣服也舍不得穿。有时候我说他,他总是说年龄大了穿好穿坏无所谓,只要干净就行。他节省下来的钱,大部分都接济了外甥和侄女等亲戚;还有的捐给了村里及社会的公益事业。他总是说,忘不了他们的父辈过去是如何帮助自己的,应该报答他们的恩情。对于村里的公益事业,他积极参与,带头捐资。村里建学校、修造梵王庙、请剧团唱戏,他捐了五万三千余元。除了经济捐赠,他常常和村里的老干部一起参政议政。看到这一切,我心里想:一天干部也没有当过的人也有了这样的意识,可能这是父亲的精神解放吧!
2002年,父亲69岁,按照乡俗,我们为父亲过70岁的生日。生日过后,我抽出时间带他去苏州和杭州旅游,让他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不久之后,我又带他去了香港、澳门旅游了一回,让他感受到了什么是现代化。每次旅游,父亲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一路上给我讲了许多。那一年我也将近40岁,对父亲也能理解一点了。
2003年元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尧都区发生的一起矿难,随后我被问责,不久就身陷囹圄。80天后我出来,见到父亲,发现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父亲看到我,大声痛哭,劝我:“想开点,做不成官别做了!工作上的事我不知道对错,但社会上的人都说你是条汉子,有这句话,爸就什么都有了!”父亲原以为这件事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年5月,《焦点访谈》对此事又追踪报道了一次,这次对他的打击最大。他以为我会再被抓进去,节目还没有看完就不会动了。送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突发脑栓塞,主要是惊吓引起的。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到深深的内疚和自责。父亲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还要为我的不当工作承受如此的伤害,真是不应该啊!
经过四年半漫长的等待,2007年8月,组织上任命我为蒲县人民政府县长助理,在父亲的眼里我是又“出山”了,他高兴地说:“就应该这样。只要恢复了,干一天都行,爸爸死了都可以瞑目了。”这时我才明白,几年来父亲劝我都是给我宽心,生怕自己的孩子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在蒲县工作了3年,父亲去看了我一次,祝愿我好好为公家干事、平平安安。2010年6月,组织上调任我为洪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到任后,父亲又专门看了我一次,并用自己的方式同样祝愿我好好为公家干事、平平安安。
今年正月,父亲一本正经地和我商量:“我想请我的老朋友们和孙曲老家的人吃顿饭,全家人都要参加。”我认真地做了准备,实现了他的愿望。后来我才明白他做事的原委,原来是过年时我和他说:“现在国家号召一切事情从简办理,你的生日怎么过我在考虑。”父亲只邀请老朋友吃饭是在做不办生日宴的准备,他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啊。
我的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和千千万万的平凡人一样。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有自己的自尊和自爱,有望子成龙的期盼和情怀。他敬老人、爱伴侣、亲孩子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作为晚辈,有时可能不会马上理解,说不定一辈子也不会完全理解,但是我们要尊重父亲,热爱父亲。父亲给予了我们生命,是他用粗茶淡饭把我们养大。父亲是我们登天的梯,是拉车的牛,是我们人生旅途上做人做事的第一位老师,我们应该永远感恩!
愿天下所有的父母安度春秋!(本文作者王青丽,系我校机电82级校友)